发布日期:2026-01-28 00:17 点击次数:52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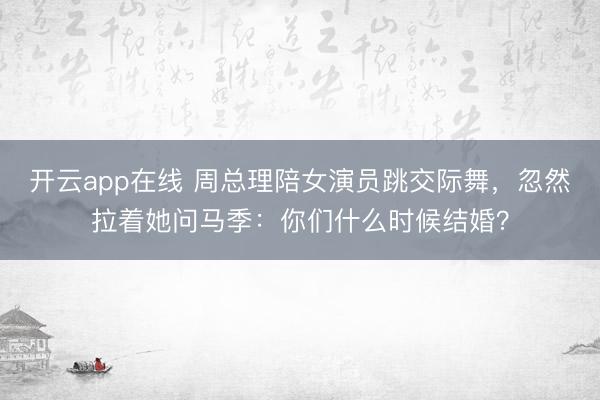
1960年10月23日晚,北京的第一场秋雨刚停,勤政殿外的梧桐叶正往下滴水。灯光洒在湿漉漉的路面上,周恩来换了一双软底皮鞋,快步穿过走廊,准备参加当晚的红墙舞会。那时的星期三、星期六,只要日程允许,中南海都会腾出一间大屋,让干部们跳几曲慢三步,舒展紧绷的神经。
舞会开始前,总理照例巡视舞池。里面有中央歌舞团、广播说唱团的演员,也有刚从会议室出来的工作人员。跟在他身后的,是一位二十出头的河南姑娘,她身着浅色旗袍,腰板挺得笔直——姑娘刚在人民大会堂说了一段《偷杏》,嗓子清脆,逗得在场首长直抹眼泪。她正是马季的女友,台里人都知道,却没人敢当面提。

说到马季,还得倒回1956年。那一年,他考进中国广播说唱团,被指定由侯宝林带教。侯先生待徒弟一向严,但心里又偏爱这个年轻人,“千亩地一根苗”这句话,他在烟雾缭绕的团长办公室里讲过不止一次。刘宝瑞、郭全宝同样惜才,三位老师轮番点拨,让马季进步极快,也让“师父吃醋”的小插曲时不时出现,圈里成了笑谈。
1958年春,中央说唱团第一次接到中南海演出邀请。通知很具体:不许上长篇政治段子,只求让首长们轻松。马季试探着上了《装小嘴》,效果奇佳。周恩来在后台轻拍他的肩:“你得记住,你们说的不是普通段子,是让大家歇口气的艺术。”那天起,马季在红墙里的出场频次直线上升。

再说回舞会。慢板探戈响起,周恩来轻轻拉起女演员的手领进舞池,节奏稳健,步点柔和。曲子换成伦巴,他看见马季靠在窗边,就笑问:“小马,怎么样?我跳得还行吧?”马季忙点头。总理忽地收了舞步,转身把姑娘带到马季面前,语气很平常,却一句戳中要害:“小马,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?你们什么时候结婚?”马季愣住,姑娘也羞得低下头。短短一句话,把公事场合捎了点人情味,气氛顿时活络起来。
舞会后,周恩来把两人领到毛泽东那边。主席刚品完一杯龙井,见状哈哈大笑:“唱‘扣帽子’的是小马的对象?怪不得台上那么尽兴。”一句玩笑,让年轻人松弛下来,也让相声圈津津乐道多年。
1961年夏,另一起小风波把马季再次推到总理面前。那年7月,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朝鲜队与八一队的足球赛,八一队一球惜败,五百多名球迷怒砸看台,还围堵裁判。事态传到钓鱼台,周恩来脸色很不好:“输球可以,闹事不行!”他直接给马季下任务:“写个段子,讽刺这股歪风,越快越好。”马季熬了两个通宵,《球场上的丑角》成稿,录音在赛前循环播放,球迷情绪果然缓和不少。

比起赛事风波,周恩来对文艺走向更为上心。1962年初冬,中央歌舞团在怀仁堂排练。台上几个陕北姑娘唱起河北小调,腔调洋味十足。总理看了半段就皱眉:“把她们调进来,是为了保留陕北民歌,不是为了赶时髦。”团长连声认错。边上观摩的马季暗自警醒:守住根脉,艺术才耐久。
{jz:field.toptypename/}马季与周恩来的交流,从来不限舞会或排练厅。一次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,请梅兰芳演《穆桂英挂帅》,中场需要短节目垫场,于世猷临时请假,马季只好单刀上阵,一段《抡弦子》说得抑扬顿挫。演毕,周恩来把他叫到座位旁:“小马,学艺得有自己的作品,光学是不够的。”这话马季记了一辈子,也成了日后坚持创作的动力。
1965年隆冬,北京又落大雪,中南海设宴犒劳说唱团。酒到微醺,侯宝林正要离席,被杨尚昆挽住再喝十七小杯。侯先生步出西门,瞧见一名收破烂汉在雪地里吃力拖麻袋,想起自己当年穷戏班的小辫子,心里一酸,掏出两块钱让三轮车把人送回家。这事被看门卫兵记下,传到团里,成了口口相传的佳话,也侧面印证了老辈艺人的善意。

同一时期,王光美邀请部分演员观摩卓别林《杀人喜剧》。胶片没配中文字幕,她边看边给刘少奇翻译。镜头扫到药瓶,“CHLOROFORM”几个英文字母闪过,她轻声嘀咕:“什么意思?”坐旁边的侯宝林小声答:“麻醉剂。”王光美惊讶,原来这位老先生不仅贯口惊人,还能读英文。小插曲令她重新审视传统曲艺人的文化底蕴。
时间推到1970年代,马季已是说唱团台柱,可他仍会回味那场秋雨过后的舞会。周恩来一句“什么时候结婚”,既是关心,又像台上精准的抖包袱,温和又到位。后来马季回忆,总理是用国家领导人的身份,保护了一对年轻人的爱情,也守护了一门古老艺术的尊严。